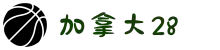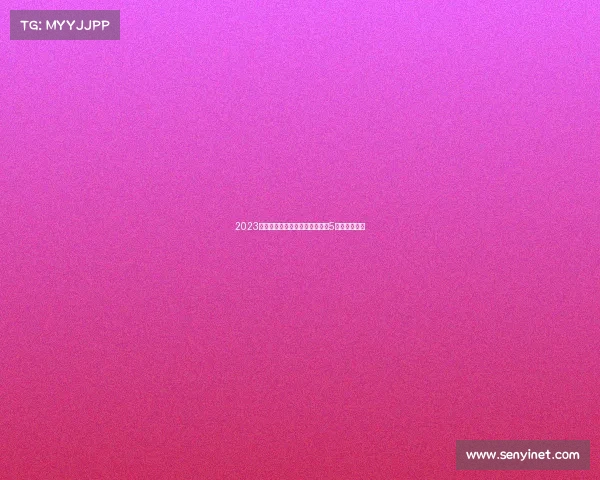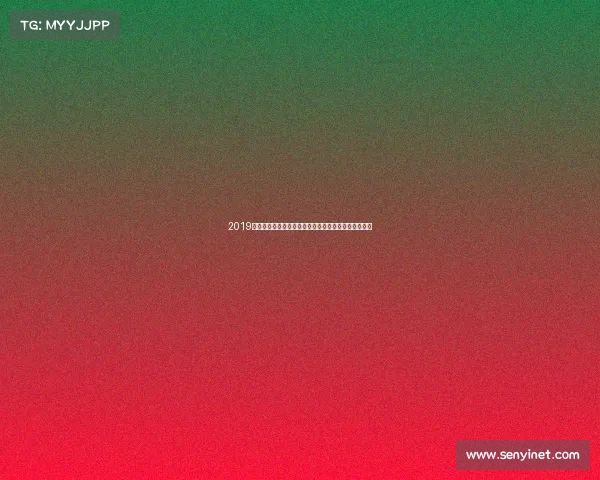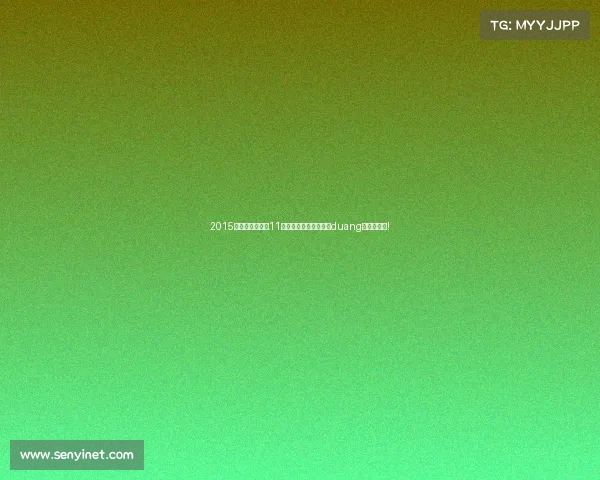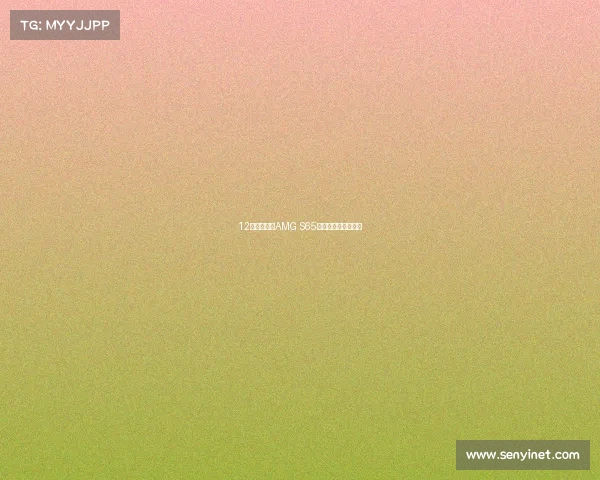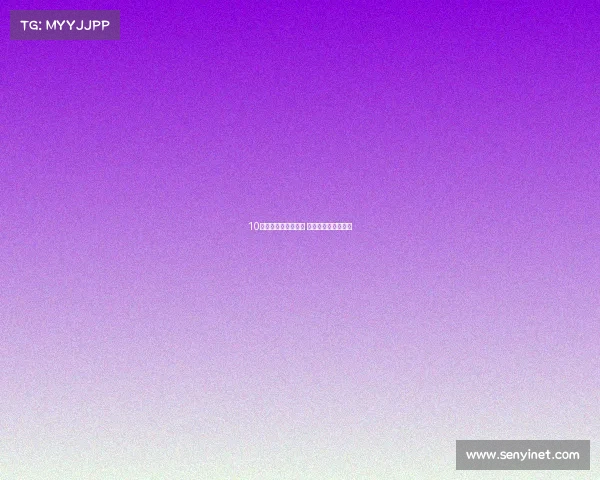4
2008年4月11日,周五,傍晚时分的华盛顿格外潮湿和沉闷,三米高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青铜雕像在财政部大楼的南门外若隐若现。这时,迪克·富尔德正大步迈过汉密尔顿身后的台阶,走进财政部大楼。富尔德应汉克·保尔森[10]的邀请前来参加G7峰会的闭幕晚宴。这次私人宴会奏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的开幕序曲。受邀者几乎都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决策者和经济学家。欧洲央行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Jean-Claude-Trichet)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以及华尔街10位首席执行官均位列其中。
此时,富尔德一改先前悲观绝望的心境,他开始乐观起来,因为两周前雷曼宣布的4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至少已暂时稳住了接连下挫的股价。另外,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尔德·贝兰克梵在公司年会上的讲话也极大地鼓舞了整个市场的信心,他认为信用危机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并断言:“危机已经到了尽头,而不是刚刚开始。”
然而,这些并不意味着笼罩在华尔街上空的阴霾真的已消散殆尽。就在当天上午,富尔德还与蒂莫西·盖特纳一起参加了一场争论颇为激烈的会议。这次会议在位于纽约市中心曼哈顿的纽约联储召开。富尔德在会上恳求盖特纳采取措施处置做空者,他认为正是这些家伙害得自己喘不过气来,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市场监管部主任埃里克·西里(Erik Sirri)却在会上反复逼问富尔德,向他索要非法交易的证据。埃里克甚至故意恳求道:“告诉我点什么吧,哪怕一个名字或者其他什么的都可以。”富尔德虽然非常恼怒,但也只得无奈地表示自己并没有掌握什么具体证据。在富尔德眼里,这位前哈佛商学院的教授无非是个自由市场的狂热信徒,没有任何实际经验,因此不屑和他多争辩。
进入财政部大楼后,富尔德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穿过由黑白棋盘格大理石铺就的走廊。此时他试着忘却所有烦恼,准备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晚宴设在财政部富丽堂皇的现金室,该室于1869年开始使用,因长期作为公众将国债兑换成现金的场所而被公众称为“现金室”,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现金室”才改做他用。最初财政部设立“现金室”的目的是为了支撑民众对南北战争时期发行的“绿币”的信心,然而近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今天公众的信心却愈显不足了。
一周以来,富尔德一直在热切期盼今晚的到来,因为他迫切希望能与保尔森进行面谈。过去几周,他曾与保尔森通过几次电话,但现在形势危急,富尔德觉得自己非常有必要与保尔森面谈一次。这样一来可以借机向财长展示自己是多么努力地挽救危局,二来可以试探雷曼在华盛顿官员心中的地位。
金融界人士缓缓地鱼贯而入,富尔德很快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位旧友——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克,他是这间屋子里为数不多的了解富尔德困难处境的人之一。在华尔街所有首席执行官当中,富尔德觉得自己与麦克最为亲近,因为他们都长期担任华尔街大投行的掌门人,并且时常携夫人一起共进晚餐。
虽然富尔德对这间屋子里的某些人并不熟悉,但他还是会停下来与他们一一握手,因为他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其中一些人很有可能会在自己的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鲍勃·戴蒙德(Bob Diamond)就是其中一位,他是美国银行家、巴克莱资本的首席执行官。巴克莱资本是英国金融巨头巴克莱银行旗下的投资银行部门。富尔德曾与戴蒙德交谈多次,但以往只是为自己热衷的慈善事业募捐而已。当富尔德跟他打招呼时,戴蒙德虽彬彬有礼但明显比较冷淡。也许是因为富尔德曾请他喝咖啡一事,当时富尔德没有意识到戴蒙德遵循的礼节标准是伦敦式而非纽约式,因此惹戴蒙德不太高兴。虽然这是个微小疏忽,但戴蒙德却一直记在心头。随后,富尔德还向戴蒙德的监管者、英国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Alistair Darling)和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表达了敬意。金融界精英层其实是个很小的圈子。不过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人们都没意识到这个圈子是多么地小。
富尔德在人群中穿行,目光时刻追随着保尔森的身影,希望能在晚宴开始前跟他说上两句。然而保尔森却主动找了过来。他穿着一套尺寸明显偏大的深蓝色西装,热情地拉住富尔德的手说:“你们确实很努力。融资也是正确之举。”
富尔德回答道:“谢谢您的肯定,我们的确一直在努力。”
加拿大网站保尔森对他们进行的另一项工作也表示了肯定,那就是此前雷曼副董事长托马斯·拉索和雷曼全球策略部负责人里克·里德(Rick Rieder)联合保尔森的副手罗伯特·斯蒂尔以及参议员贾德·格雷格(Judd Gregg)举行了一次“颇有见地”的会谈。其间,拉索提议政府组建一个为金融系统增加额外流动性的专门机构,从而为华尔街众多公司的“有毒资产”提供后盾。但该提议最终遭到否决,因为这看上去又像是一次政府救援行动,而华盛顿完全没有做好相关准备。
保尔森对富尔德说“很多事情都让我非常担心”,他这话针对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该报告宣称未来两年内抵押贷款和房地产相关资产的减值总额预计将高达9 450亿美元。另外,保尔森对当前极高的杠杆率(负债权益比率)也非常担忧,他认为这只会使整个金融体系承受更大的风险。但投行仍在利用高杠杆来放大盈利水平。
华尔街投行的杠杆率的确令人担忧。比如,雷曼的杠杆率高达30.7:1,美林稍低一些,但也达到了26.9:1。保尔森知道,美林与雷曼一样深陷有毒资产的泥潭,他曾提醒美林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塞恩(保尔森担任高盛首席执行官时,塞恩还是二把手),美林的资产负债表正面临着严峻挑战。但此时此刻,高杠杆率和美林的困境并不是富尔德最关心的问题,最让他烦心的仍是那些做空者,所以他再次恳求保尔森对做空者采取行动。一旦把他们制服了,雷曼和其他公司就有机会站稳脚跟,改善资产负债表。否则,如果任由他们恣意妄为,整个局势将会变得更加糟糕。
曾经当过首席执行官的保尔森能够理解富尔德的心情,做空者只关心自己的收益,而全然不顾他们的做法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于是他对富尔德说:“我非常同情你的处境,一旦发现违反规定的做空行为,我们会及时制止。”
但同时保尔森也担心富尔德是借做空者来回避雷曼真正的问题,所以他接着提醒富尔德,雷曼潜在的买家可能会很少。“你要清楚,尽管融资的做法不错,但是能解决的问题有限,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保尔森继续补充说:“迪克,现在并没有多少人表示‘我非常需要一家投行的特许经营权’,所以你必须考虑雷曼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暗示,意思是让富尔德考虑出售整个雷曼。虽然这次面谈让富尔德感到有些不安,但因为此前他们已谈论过类似的话题,所以他还是能够平静地接受这些建议的。
来宾落座后,随着各位演讲嘉宾发言的进行,大家发现经济形势的危局已十分清晰。这次信用危机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它已经扩散到了全球。意大利央行行长、高盛前合伙人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坦率地表达了他对全球货币市场基金的担忧。特里谢则表示,希望大家能够在相关资金比率(一家机构须持有和借出资金的比例)、杠杆率和流动性标准上达成一致,他认为这些指标能够更有效地衡量金融机构抵御挤兑风险的能力。
当天晚上9点52分,当富尔德走出财政部大楼并坐上车后,他用黑莓手机给拉索发了封邮件:
保尔森的晚宴刚刚结束。
有这么几点需要跟你提一下:
1.我们拥有巨大的品牌价值。
2.保尔森肯定了我们融资的做法。
3.十分赞赏你和里克·里德的看法(他原话如此)。
4.准备处理一些行为不轨的对冲基金,并严格监管其他的对冲基金。
5.他们希望所有G7成员国都能接受并制定如下条款:
逐日盯市标准;
资金比率标准;
杠杆标准与流动性标准。
6.保尔森对美林表示担忧。
总而言之,参加这次晚宴非常值得。
迪克
晚宴之后的星期二,也就是4月15日,尼尔·卡斯卡里和菲利普·斯瓦格于下午2点50分左右快步经过警卫室,匆忙地走下财政部大楼的台阶。他们如此紧张是因为保尔森和罗伯特·斯蒂尔正坐在保尔森黑色的雪佛兰萨博班小轿车里等他们,他们4位要在3点赶到美联储,现在还剩10分钟,显然已经要迟到了。
卡斯卡里和斯瓦格两人凑在一起显得有点古怪。秃顶的卡斯卡里皮肤呈浅黑色,也许是转行不久的缘故,他仍旧是一副投行人士的扮相。再看斯瓦格,白皙的皮肤,棕黑的头发,还带着副眼镜,看起来更像个不靠谱的政府官员。斯瓦格之前是个学者,保养得很好,虽然他实际上比34岁的卡斯卡里大8岁,但看起来却更为年轻。
保尔森让这两位年轻顾问与本·伯南克会面,是为了让他们陈述一下他们所起草的一份秘密备忘录。对于美国日益动荡的金融体系来说,这份备忘录可谓意义深远。
按照保尔森的要求,他们起草了一份金融市场崩溃的应急计划以防止大萧条再次发生,其中概述了财政部可能采取的行动以及必要的授权。他们给这份建议书起了个颇具煽动性的名字:“击碎玻璃:银行资本重组计划。”这份计划就像是封闭在玻璃后面的防火警报,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把玻璃击碎,取出里面的灭火设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计划书的内容越来越像是真的,而不仅仅只是一种演习了。
卡斯卡里天生不易激动,当黑色萨博班小轿车驶入伯南克官邸时,他仍旧十分镇静。在做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卫星工程师后,卡斯卡里去了旧金山的高盛,成为一名投资银行家,并在那里如鱼得水。他喜欢见客户,并在工作中充分展现了他的推销能力。和保尔森一样,他也是个争强好胜、雷厉风行的家伙。同样,有时他也会像保尔森一样因先斩后奏的行事方式而惹上麻烦,但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他非凡的智慧。
卡斯卡里一直向往政府部门的工作。虽然他之前只见过保尔森一面,但是当保尔森被提名为财政部长时,他立刻发了封语音邮件表示祝贺。令他惊喜不已的是,保尔森第二天就给了他回复:“谢谢,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加入财政部。”
卡斯卡里马上订了张飞往华盛顿的机票。在飞机上,他一丝不苟地排练着与保尔森的对话。后来,他们在旧行政办公大楼碰了面,因为保尔森还在等待参议院的正式任命,所以只能临时待在这里。卡斯卡里精心准备的长篇大论刚刚开了个头,就发现保尔森脸上露出了不耐烦的表情,他立马知趣地闭了嘴。
保尔森对他说:“你看,我在这里做的事情是这样的,组建一个小型团队负责政策方面的工作,实际上,这个团队需要随时解决方方面面的问题以保证政策顺利实施。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
卡斯卡里非常惊讶,他马上意识到:“保尔森居然主动向我提供工作!”
他们一拍即合。保尔森突然想到一个重要的细节问题,他问道:“噢,对了,还有一个问题,你是共和党的吗?”所幸卡斯卡里刚好是共和党。保尔森让他马上去几个街区之外的白宫人事部门报到,还亲自送他出门并给他指路。卡斯卡里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小组,现在他正摩拳擦掌,准备做他职业生涯以来最大的一笔大买卖——向全球经济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人进行推销。
自2006年2月10日上任以来,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一直被四个字所折磨——“后无来者”。艾伦·格林斯潘卸任时,声誉卓著的《华盛顿邮报》专业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曾给予其“艺术大师”的称号,这或许也算是实至名归吧。格林斯潘之于货币政策有如沃伦·巴菲特之于投资,他执掌美联储期间,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从里根任期开始,一个蔚为壮观的大牛市持续了20多年。虽然并非经济圈外的每个人都时时关注着格林斯潘的一举一动,可他在解释货币政策时的模糊措辞的确是个传奇,这也给才智非凡的格林斯潘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与此相反,伯南克此前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学里当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是大萧条,美联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次大萧条中犯了大错。可是当他被任命接替80岁的格林斯潘时,他的研究领域看起来就比较古怪了。虽然找出大萧条的起因堪称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圣杯,但在民众看来,这对于担任如此关键的政府职位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从过去的历史来看,那种程度的经济危机似乎不太可能再度发生了。
然而到了2007年夏天,美国的第二个“镀金年代”惊人般地画上了休止符,格林斯潘的声望也随之跌入深渊。此时,格林斯潘的信条“市场将会自我修复”突然显得如此苍白和浅薄,事后诸葛亮们更是指责他那些隐晦的言辞完全是东拉西扯、误导大家的废话。
虽然伯南克和格林斯潘一样信奉自由市场,但是作为一名研究大萧条的学者,他与格林斯潘有所不同。伯南克在大萧条的研究中进一步发展了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Anna J. Schwartz)的观点。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认为,大萧条的发生是因为美联储当时没有立刻向整个经济体系注入足量的廉价货币来刺激经济,并且后续的努力又太少太迟。当时,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政府时期的美联储所采取的措施恰恰背道而驰:收紧货币供给,彻底扼杀了经济。
由于伯南克根深蒂固的学术观点,许多观察者都对其担任联储主席一职的前景感到乐观,相信他将是一位独立的联储主席,会坚持做他认为对的事而不是被政客所左右。这次信贷危机可谓是伯南克所面临的第一次重大现实考验。他对80年前那次经济政策失误的理解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他化解当前的危机呢?毕竟,他面对的不是历史,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伯南克出生于1953年,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小镇狄龙(Dillon)长大。狄龙有许多烟草仓库,空气里始终弥漫着一股恶臭。1965年,11岁的伯南克到华盛顿参加全国拼写锦标赛,在第二轮的时候因为拼错了“Edelweiss”(雪绒花)而被淘汰出局。那天以后,伯南克也许会想,要是电影《音乐之声》在偏远的狄龙上演过该有多好(《音乐之声》里的一首著名歌曲就叫《雪绒花》)。
伯南克家族是恪守教规的犹太人,他们所在的小镇信奉保守的福音派基督教,该小镇是从种族隔离时期才开始兴旺起来的。20世纪40年代初,本·伯南克的祖父乔纳斯·伯南克(Jonas Bernanke)从奥地利移民到狄龙,在当地开了家药店。本的父亲一直帮忙打理那家药店,母亲则是一位教师。年少的本每周在州际95号公路边一家称作南部边境的旅游点餐厅做6天的服务生。
本·伯南克上中学时,学校不开微积分这门课,他就自学了微积分。三年级时,他的SATS成绩几乎是满分(1590分)[11]。第二年,伯南克被哈佛大学录取并获得国家奖学金,后来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紧接着他又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在那里,他写了一篇极为深奥的有关经济周期的学位论文,并将这篇论文献给了父母和妻子。伯南克的妻子安娜·弗里德曼(Anna Friedmann)于1978年从卫尔斯利女子学院毕业,就在毕业的那个周末,她嫁给了伯南克。
伯南克毕业后,这对新人搬到了加州,伯南克在斯坦福商学院任教,他的妻子则在斯坦福大学教授研究生的西班牙语课程。6年后,伯南克被授予普林斯顿经济学系的终身教职。当时,这位31岁的新星因为计量经济学(运用统计技术和计算机模型分析经济问题的学科)的研究而受众人钦佩。
随着伯南克学术声望的提高,他的政治能力也开始逐步展现。担任普林斯顿经济学系主任期间,伯南克表现出了有效解决纠纷与自我平衡的能力。此外,他还发起了一些新项目,为学校招募了一批包括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他和伯南克的学术观点恰好相反)在内的颇具前途的经济学家。6年后,伯南克便被任命接替格林斯潘。
2007年8月初以前,伯南克一直很享受在美联储的工作,生活得非常闲适。他和妻子安娜还打算当月一起外出度假,先驾车去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然后再去南卡罗来纳州的默特尔海滩,花些时间与家人朋友们待在一起。南行之前,伯南克必须完成一项既定的公事:参加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定于8月7日的会议。公开市场委员会在政策制定方面的权力非常大,在它所负责的众多事务中,有一项是决定利率。当天,伯南克和同事们开始意识到关于“经济下行风险”的问题,不过,他们最终还是决定保持5.25%的美联储基准利率不变,这已经是美联储连续第九次表明将坚持一贯的立场,不会通过降息来提升经济活力。联储还在随后的声明中表示:“如果通货膨胀率不能达到预期的适度水平,委员会的政策仍将优先考虑通胀风险。”
华尔街可不想听到这些,由于担心经济崩溃,投资者们正大吵大嚷着要求降息。4天前,在CNBC下午时段的一档节目中,金融评论员吉姆·克拉默大发雷霆,指责美联储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措施,他还激动地喊道:“他们真是一帮傻瓜!什么都不知道!”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被逐渐挤出,信用市场的情况开始变得日益严峻。这一点联储的决策者很清楚,只不过没有将其公之于众。低息信贷可谓是经济发展的火箭燃料,廉价的资金成本会刺激消费者大量借贷——购置第二套房产、购买新车、翻新房屋或者度假旅行。另外,低息信贷还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交易狂潮:私募股权基金借入大量资金,导致杠杆收购规模变得越来越庞大,风险也与日俱增。捐赠基金和养老基金等都属于传统意义上比较保守的机构投资者,但迫于投资回报的压力,它们也不得不投资于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美联储之所以不对降息要求作出回应,是因为降息无异于火上浇油。
就在两天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8月9日早上,金融界开始出现极度危险的信号,法国最大的银行巴黎银行宣布旗下资产规模大约为20亿美元的3家货币市场基金暂停向投资者提供赎回。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实际上,部分资产市场的流动性已经枯竭,其中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市场的情况尤为严重,而这导致该类资产的实际价值难以确定。巴黎银行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资产证券化市场中部分领域的流动性已经彻底丧失,无论相关资产的质量和信用程度如何,目前该类资产无法进行合理定价。”
这是一个令人胆寒的信号,对于抵押贷款的相关资产,交易者很快就避之唯恐不及,无论什么价格都不愿购买。欧洲央行迅速对此作出反应,向欧洲货币市场投放了950亿欧元,即1 300亿美元的资金。这个数额比“9·11”之后所投放的还要大。同时,全美最大的抵押贷款机构——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发出警告:目前“前所未有的崩溃”市场已威胁到公司的财务状况。
银行间拆借利率应声大涨,远远超过央行规定的官方利率。对于伯南克来说,这一切再明显不过了:这是一场金融恐慌。银行和投资者生怕沾上这些有毒资产,转而大量持有货币,并几乎不进行任何形式的放贷。由于很难弄清各家银行次级贷款的风险敞口,因此在证明清白之前,所有银行都被认为是有问题的。20世纪30年代初的各种特征都已经被重现——流动性瞬间蒸发,全球金融体系的信心被迅速消蚀。这不禁让人想起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的名言:“每一位银行家都清楚,当他不得不证明自己是可信的时候,不管他说得有多好听,实际上他已经没有信用可言了。”
伯南克通知妻子,他们的旅行计划不得不取消了。随后,他便把以前通常是电话联系的顾问们都召集到了办公室。美联储的官员们开始举行电话会议,试着搞清楚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哪些机构可能需要帮助。此后,伯南克每天早晨7点以前就到达办公室。
仅仅两天之后,市场再次发生震荡,形势开始急转直下,美联储每天都忙于应付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第二天,伯南克召开电话会议与美联储的决策者商讨降低再贴现率(再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向央行直接借贷时的利率,通常是一个货币政策松紧的信号)。最后,美联储决定发布声明:放宽银行抵押品的种类限制,便于银行获得资金。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来提供流动性,以帮助市场功能尽量恢复正常。虽然这项举措的力度要小于欧洲央行,可这也提醒了银行可以通过“再贴现窗口”这个途径获取资金。在这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面对持续恶化的市场状况,伯南克改变了此前的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将再贴现率降低0.5%至4.75%,这一举动暗示着美联储可能将调低基准利率,这是联储刺激经济最有力的工具。但是,尽管美联储出台了这些措施来帮助恢复市场信心,整个市场仍然神经紧绷、波动剧烈。
至此,伯南克也认识到,自己之前对形势的严峻性估计不足。6月5日,他甚至在一次演讲中宣称:“目前看来,次贷市场的问题不会扩散至其他经济领域,也不会危及金融体系。”对于房地产市场,他一度认为发生问题的仅限于那些向低信用借款者发放的次级贷款,尽管次贷市场已迅速增长至2万亿美元的规模,但相对于整个美国14万亿美元的房屋抵押贷款市场,这些还只是一小部分,因此问题不大。
但伯南克忽略了其他重要因素:由于复杂金融衍生产品的使用日益增长,房地产市场与金融体系的关系已非常复杂。大量的房屋抵押贷款被证券化,在成为具有一定现金流的证券后,经过重新分类组合和再次分拆,它们很快就变成了颇具吸引力的投资产品,并被冠以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的名号。
摩根大通和雷曼这类公司的业务模式已经和传统银行大不相同,再也不只是简单地发放贷款,然后将其计入资产负债表。以现在的模式,作为业务开端的贷款只是资产证券化链条的第一环,随后贷款的风险就可以通过证券化的其他环节分散传递到无数的市场参与者那里。一般认为,证券化可以降低风险并增加流动性,但实际上证券化使得众多机构和投资者的联系更加紧密,这种结果有利有弊。比如,挪威一家地方政府养老基金的投资组合可以包括加州的次级抵押贷款,但这家养老金却可能对此一无所知。更为糟糕的是,许多金融机构为放大收益而大举借债以投资这类证券。而这种做法只会在这些证券开始贬值时,令他们的损失雪上加霜。
全球的监管者都很难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格林斯潘承认他也不大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他在卸任两年后的一次讲话中表示:“虽然我有相当深厚的数学背景,但是一些用于构造担保债务凭证的复杂衍生工具还是让我感到非常困惑。我不明白他们在实务中如何计算不同层级担保债务凭证的收益。要知道,我有两百个博士做顾问,如果连我都弄不明白,那么很难想象世界上的其他人是怎么弄明白这些产品的。”
不只是格林斯潘,那些销售这些产品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也没弄明白。
美联储主席办公室的门敞开着,伯南克热情地欢迎到访的财政部小组。与斯瓦格一样,伯南克看起来更像是个学者,但对一名经济学家而言,他客套的寒暄做得很漂亮。他把保尔森一行领进办公室,并在一张小咖啡桌前落座。除了必备的彭博终端外,一顶华盛顿国民队的棒球帽也显眼地摆在伯南克的办公桌上。谈了几分钟之后,斯瓦格从文件夹里取出那份题为“击碎玻璃”的10页报告书,战战兢兢地把它递给伯南克。卡斯卡里扫了一眼他的同事以确定自己可以开口说话。
“我认为我们都很清楚政策问题的症结所在,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内我们可以做的事非常有限,此时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获得足够的授权来防止市场的崩溃,”伯南克点头对此表示同意,于是卡斯卡里继续说道,“如您所知,在过去几个月里,财政部和美联储的相关人员一直在研究一些可行方案,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框架。这意味着一旦面临严重的混乱,在紧急情况下我们可以立即把方案提交给国会并对他们说‘这是我们的应对计划’。”
伯南克全神贯注地研读报告,卡斯卡里则注视着伯南克,期待着他的评价。突然,伯南克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份计划的关键点上:“美联储通过拍卖机制向金融机构购买5 000亿美元的资产,如何给这些繁杂的证券定价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另外,美联储还将通过发行新的国债来补贴购买者,并雇用私人部门的资产管理者以实现这些纳税人资金的保值增值,最终解决那些问题资产可能需要10年时间。那么,5 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出来的?”
卡斯卡里回答说:“这么说吧,我们大致估计了一下,有毒资产的规模大概是1万亿美元,为了有效拯救市场,我们并不需要把它们全都买下来,我们认为购买一半应该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可能会超过6 000亿美元。”
伯南克继续研究他们的报告,卡斯卡里和斯瓦格静候着,体验着这特殊时刻:他们在向美联储的掌门人解释这份可能被载入史册的针对银行系统的救援计划。近50年里,政府从未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干预,与之相比,20世纪80年代的储蓄贷款救援计划亦显得微不足道。
假如“击碎玻璃”计划能在国会通过(这是他们下一步需要解决的事情),他们还相应地准备了财政部委托纽约联储对华尔街有毒资产进行拍卖的详细方案。财政部将从私人部门招募合格的投资人来管理政府购买的这些资产。纽约联储将就标的约为500亿美元的房屋抵押贷款相关资产进行第一周的拍卖,而总的拍卖期限为10周。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拍卖将使政府获得最为合适的价格。而10位入选的资产管理人将分别负责管理500亿美元的资产,最高期限为10年。
卡斯卡里知道这个提议非常复杂,但他认为这值得冒险一试。因为随着事态的发展,“软着陆”的可能性已经比较渺茫,所以很有必要采取极端措施。他解释说:“这个提议需要相关法案授权财政部购买那些证券并进行相关融资,而且需要提高财政部发债的上限,因为在当前的限定下,我们只有4 000亿美元的融资空间。因为这次我们对私人部门的干预力度很大,所以这项计划不能再占用过多的政府经费,比如财政部就没有因此雇用大量人员。我们也要注意相关限制条件,即只有上市公司才有资格接受援助,对冲基金和国外银行则不在其列。”
随后,卡斯卡里总结了他与财政部同事们共同归纳的这项提议的利弊方面。主要的有利之处是如果政府出手救援,银行将继续放贷,不会因为政府的不作为而在第一时间引发危机。主要的问题则是,如果这项计划的实施卓有成效,那么很有可能导致“道德风险”。换句话说,这场危机是由那些不计后果豪赌的人所引起的,而正是因为政府的救援,他们无需付出任何财务上的代价。
这两位财政部官员还提出了4项替代方案:
一是政府向银行提供担保,防止其有毒资产减值;
二是美联储向银行提供无追索权的贷款(如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时美联储所采取的措施);
三是美联储房地产主管部门个别地提供贷款再融资;
四是财政部直接投资于银行。
伯南克一边听着一边摸着胡子,时不时露出微笑以示赞同。会议结束时,除了这项计划获得通过外,并未形成其他任何正式决议。尽管这项计划实际上仅作为应急计划,但卡斯卡里仍感到非常满意,因为与亨利·保尔森比起来,伯南克算是很快接受了他的提议。他当初向保尔森提及干预金融市场的话题时,保尔森根本没理他的茬儿。
保尔森在财政部的核心成员都知道这件事。三月份的一天深夜,卡斯卡里冒冒失失地闯进保尔森的办公室,当时保尔森正在与首席顾问詹姆斯·威尔金森聊天,看起来心情非常好。
卡斯卡里很不礼貌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汉克,我想和你谈谈紧急援助的事情。”
保尔森立马变得恼怒起来:“你说什么?你给我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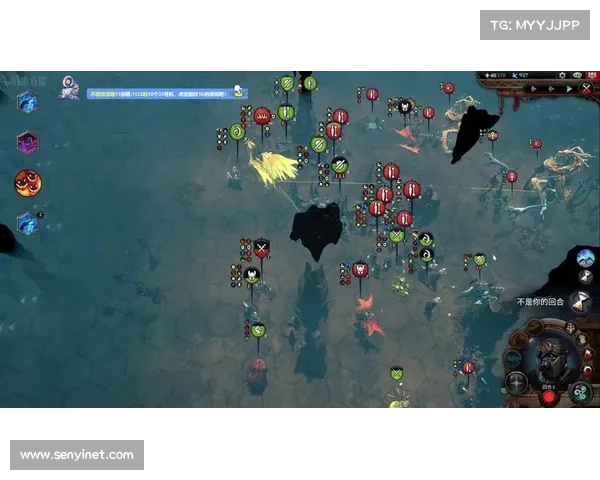
“你看,我们一直在谈论如何才能获得政治意愿方面的支持,以便在真正采取行动时能得到相应的权力。是这样吧?那么,这就需要有记录来显示我们的确为此做过努力。否则,下届总统上任时就会说‘当时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前任政府没有意愿或者根本没有能力来采取行动’,等等诸如此类的话。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下届总统将会把人质带回家的。奥巴马!奥巴马将会把人质带回家!”
卡斯卡里是指奥巴马会像20世纪70年代末罗纳德·里根处理伊朗人质危机一样处理这次危机。听到这,保尔森冷笑着打断了卡斯卡里,并用手指指着他说:“好吧,奥巴马会把人质带回家。你说完了吗?说完了就给我滚出去!”
4月的一天,傍晚时分的伦敦上空飘着几片灰云,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这时,巴克莱资本的首席执行官鲍勃·戴蒙德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他此时正在办公室里惬意地琢磨着推杆技术,一堆高尔夫球散落在球洞周围,球洞则是在办公室地毯上裁出来的。戴蒙德的办公室位于金融机构聚集的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这个伦敦东部极为繁华的金融区被称作伦敦金融城。虽然戴蒙德是土生土长的新英格兰人,但他却是波士顿红袜队的铁杆球迷,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红袜队的各种纪念品。如果看到这些琳琅满目的纪念品,恐怕连纽约人也会感到自惭形秽(纽约有很多红袜队的球迷)。
戴蒙德一向不喜欢在宝贵的休息时间被打扰,但这回他却欣然地放下推杆接了电话:因为电话是他的老朋友罗伯特·斯蒂尔打来的,前些天他们还在华盛顿财政部大楼的晚宴上见过面。
2005年,戴蒙德和斯蒂尔同时加入巴克莱董事会,后来逐渐成了亲密朋友。他们来自美国的不同地区,擅长的工作领域也不同。斯蒂尔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Durham),之前在高盛的股票交易部工作;戴蒙德则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以前曾在摩根士丹利和瑞士信贷担任债券交易的主管。但他们也有共同点:两人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都是从大学一步步努力才走到今天的。
最近一段时间,两人职业生涯轨迹尤为相像:作为英女王伊丽莎白辖下的“美国佬”,斯蒂尔和戴蒙德在伦敦都大有作为。在加入高盛欧洲的股票交易部后,斯蒂尔立下了丰功伟绩,他之前的老板保尔森一直对此印象深刻。戴蒙德则把一家仅有3 000人的小投行发展成在伦敦拥有15 000名雇员的强大集团,现在巴克莱资本所创造的利润占整家银行利润的25%。
斯蒂尔辞掉巴克莱董事一职后,追随保尔森去了美国财政部,但他和戴蒙德依旧保持着很好的朋友关系,不管什么事,只要一方打电话,另一方准会立即接听。
斯蒂尔跟戴蒙德打完招呼后,略显生硬地说道:“是这样的,我们正在广泛征求意见,以制定应对各种危机情况的有效措施,我想向你请教一下。”
斯蒂尔这种一反常态的客气语气让戴蒙德有些吃惊,他问:“斯蒂尔,是政府的事吗?”
斯蒂尔回答说:“不,不是的。我找你并不代表任何一方。现在市场稍微缓和些了,但是我想搞清楚,形势会不会变糟。因为如果形势很不利,将会有大麻烦。”
“那好,你问吧。”
斯蒂尔做了个深呼吸,然后缓缓问道:“在什么价位你才会对雷曼感兴趣?如果打算收购,你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戴蒙德一时语塞,他意识到,美国财政部很明显是在为雷曼打造一个战略解决方案,这样当雷曼身陷类似贝尔斯登的处境时才能为其找到出路。经过长时间的接触,戴蒙德清楚斯蒂尔不是一个无聊又爱管闲事的人,更不会无事生非。
戴蒙德谨慎地回答道:“这太突然了,我得仔细考虑一下,因为现在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
斯蒂尔说:“好的,但请务必好好考虑一下。”
“凡事无绝对,一切皆有可能。”戴蒙德回答道,然后两人都大笑了起来。以前每当记者追问戴蒙德某项并购有无可能时,他总喜欢抛出这句话,不过斯蒂尔倒是头一次听他这么说。
斯蒂尔深知巴克莱资本一直希望能够扩大在美国的市场份额,戴蒙德甚至曾把这份雄心壮志标在他那身在萨维尔街定做的昂贵西装的袖子上。虽然他白手起家创建了一家如今已成为伦敦代表性事物之一的大型投资银行,但他一直渴望成为华尔街主要投行的领袖之一。正是因为对这个目标的不懈追求,戴蒙德才会在1992年突然从摩根士丹利跳槽到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公司(一家全球性的投资银行和金融服务公司),并带走了众多回购协议交易员,这曾令约翰·麦克大为光火。4年后,戴蒙德又来到了巴克莱(BZW)[12],他带来的旧部又成为巴克莱资本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人力资源。
如果戴蒙德、他的老板以及位于伦敦的董事会都希望巴克莱一夜之间成为纽约一家大投资银行的话,那么雷曼是个不错的并购对象。但他也知道,因为迪克·富尔德掌管着雷曼,这必将是一次昂贵的并购。尽管如此,总的来说这仍是个难得的机会。
与此同时,巴克莱正在考虑另一项并购交易:戴蒙德已经和瑞银集团商洽,打算购买其投资银行部的特许经营权。他已决定在一周内亲自飞往苏黎世进行深入谈判。戴蒙德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斯蒂尔并提醒他,自己和瑞银集团的谈判刚刚开始,因此不要往外泄露消息,说不定这笔交易最终将不了了之。
不管怎么说,雷曼毕竟是一家重量级的投行,戴蒙德向董事会推销这样一笔大规模的并购并不容易。几个月前巴克莱斥巨资参与荷兰银行的竞标战败北之后,董事们至今倍受打击,所以他们对这次并购也犹豫不决。但雷曼是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如果低价出售,戴蒙德必须得好好考虑一下,毕竟机会难得。
“是啊,”戴蒙德对斯蒂尔说,“这绝对需要好好考虑。”